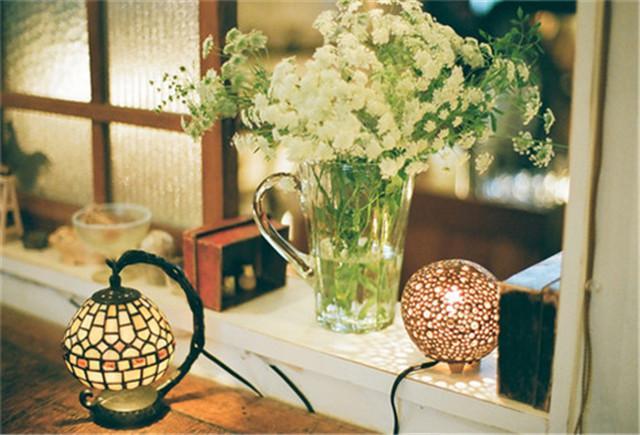古人名字(古人名字解詁)
古代人的名字:“名字”一詞,在古代代包括“姓”、“名”、“字”三個部分,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,是三個各自獨立而又相...
古代人的名字
:“名字”一詞,在古代代包括“姓”、“名”、“字”三個部分,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,是三個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
古人剛生下不久就有了名,長大以后要取字,兩者相連,通稱名字。關于二者的作用,清朝人王應奎曾說:“古者名以正體,字以表德。”意思是說,名是用來區分彼此的,字則是表示德行的。二者性質不同,用途也不大一樣。一般說來,古時候,名是階段性的稱呼,小時候稱小名,大了叫大名。等有了字,名就成了應該避諱的東西,相稱時也只能稱字而不稱名。
名與字在多數情況下共同構成一個人的代號,盡管用途不盡相同,二者之間還是有聯系的。古人大多因名取字,名與字內容毫不相干的情況幾乎見不到。如三國時的名將張飛,字翼德,在這—名字中,
“飛”是名, “翼德”則是對“飛”的解釋,因為
“飛”就是“翼之德”(翅膀扇動而造就的功德)。又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,字樂天,名與字之間也有聯系,即“居易”是因,“樂天”是果,只有居處安寧,才能知命而樂天。
古人的名有多種種類,字也有不同用途。起初,人們取字非常簡單,往往只取一字,與“子”、“伯”、“仲”、“甫”等表示年齡階段的字相連。如孔子弟子顏回字子淵,冉耕字伯牛,冉雍字仲弓,這些名字中的“淵”、“牛”、“弓”就是他們的字。當然,有些人取字時干脆只用一字,不加別的字辭,如陳勝字涉,項羽字籍等即是。東漢以后,人名取字才越來越

古人除有名、字外,又多取號以代替名字。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,又稱“別號”。早在周朝時,人們就已經開始取號。對此,《周禮》解釋說,號為“尊其名更為美稱焉”,意思是說,號是人在名、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。早期的號具有這一特點,有號的人多是那些圣賢雅士。如老子別號廣成子、范蠡別號鴟夷子皮等。先秦時期有名字又有號的人并不太多,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,取號的人仍不很多,名載史籍者僅有陶潛別名五柳先生、葛洪別號抱樸子等數人。但是,到了隋唐時期,伴隨著封建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達,在名、字之外另取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。如李白號青蓮居士、杜甫號少陵野老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,皆屬此類。到了宋代,取號之風又有進一步的發展。人們熟知的《水滸傳》108將個個都有別號,正是代表著當時的社會風氣。明清人更把取號視為一種時髦,上至皇帝,下至一般黎民百姓,幾乎人人有號。正如清人凌楊藻在《蠡勺編》一書中記載的那樣,其時“閭市村壟,嵬人瑣夫,不識字者莫不有號,兼之庸鄙狂怪,松蘭泉石,一坐百犯;又兄‘山’弟則必‘水’,伯‘松’則仲必‘竹’,不尤大可笑也哉。近聞婦人亦有之,向見人稱‘冰壺老拙’,乃嫠媼也”。甚至一些落草為寇的盜賊也有別號。如上述書中舉了一個縣官審案的例子,就十分能說明問題。這一例子說,一位縣官在審理一樁竊案時,責難犯人為自己開脫罪責,犯人突然說道:“守愚不敢。”縣官不解其意,一問左右,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稱別號。
在用字上,取號與取名、字不同,大多不受字數多少的限制。從已知的歷代別號來看,有2字號,也有3字、4字號,甚至還有10余字、20余字的別號。如清代畫家鄭板橋的別號就有12字,即“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”。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釋成

因為古人取號有較大的隨意性,并且不必加以避諱,因此,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飽受文字獄和避諱之苦的明清人,促使他們在名字之外更取別號來表現自己。當時的大多數人都取一個別號,但有些人的別號也有好幾個。如清初畫家石濤法名弘濟,別號清湘道人、苦瓜和尚、大滌子、瞎尊者,達4個之多。
綜上可知,我國古人的稱謂遠比現代人復雜,他們有姓名又有字、號。這種姓名字號的并存,既適應了當事人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情況下的需要,也為中國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。古代人起名字和現在差不了多少~只是那時是封建社會人們都比較迷信~!
給孩子起名字只有一點名子里邊 不能有在世三代以內人的名字里邊得子~!古代代包括“姓”、“名”、“字”三個部分,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,是三個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
有一個字號!
古人名字
大凡讀過《后漢書》與《三國志》的人都知道東漢、三國時期的人物絕大多數都是單名,此之前朝(周秦、西漢),單名使用的頻率更高。東漢從光武帝劉秀到漢獻帝劉協13帝全系單名,他們是劉秀、劉莊、劉怛、劉肇、劉隆、劉祜、劉保、劉炳、劉纘、劉志、劉宏、劉辯、劉協。西漢皇帝中至少還有劉弗陵、劉箕子(劉銜)二人是復名,東漢皇帝居然一個也沒有。
三國時的曹魏政權,曹操、曹丕、曹睿、曹芳、曹髦、曹奐都是單名;蜀漢政權,劉備、劉禪也是單名;東吳政權孫權、孫亮、孫休、孫和、孫皓也全是單名。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國人物如諸葛亮、關羽、張飛、趙云、孫堅、孫策、周瑜、魯肅、黃忠、馬超、袁紹、袁術、呂布、王佐、蔣干、夏侯淳、黃蓋、陸遜、許褚、張遼、孟獲、馬稷、姜維、司馬懿、司馬昭、鄧艾、華陀等,無一不是單名。 “建安七子”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禹、應瑒、劉楨與“竹林七賢”嵇康、阮籍、山濤、向秀、阮咸、王戎、劉伶,亦全系單名。間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,但甚罕見。或為隱逸,如龐德公、鄧盧敘等;或為藝人,如東方安世等;或為乳名不改,如劉盆子、鄭小同等;或單稱其字,如黃承彥、茍巨伯之屬。 東漢(25-220年)、三國(220-265年)時期約有240年左右,如果再加上三國歸于統一的西晉(265-316年),這一階段約占300年。從中國姓名史考察,這300年是中國人盛行單名的第一個高峰時期。
以前一般解釋為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復古改制,“令中國不得有二名”所致。今人馬來西亞學者蕭遙天也采此說,蕭氏在其(中國人名的研究)中說:“近讀《漢書?王莽傳》,始知單名之俗,出于王莽的倡導。原來莽輔政,便實施二名之禁,莽傳有‘匈奴單于,順制作,去二名’語,則二名之禁已見于詔令。莽又謂他的長孫王宗,因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,刻銅印三顆,與其舅合謀,有承繼祖父大統的企圖,事發,宗自殺,仍遭罪遣。有‘宗本名會宗,以制作去二名,今復名會宗。’并貶官爵,改封號。這又表示去二名,是示朝廷的寵遇,恢復二名,則以示貶辱。這么地一抑一揚,一褒一貶,對社會的影響便大了,至少造成人們對二名存在著低賤的觀念。故王莽的政權十幾年便下臺,而去二名的習慣一直維持了三百年,便是魏晉以后,單名仍較二名為多呢。”王莽的“二名之禁”造成東漢、三國乃至西晉三百余年的單名大倡,這一觀點或可自圓其說,故錄以備存。
但是,王莽政權介乎兩漢之間,僅僅只有短短的15年(9—23年)時間。盡管王莽打著“奉天命”的旗號,雷厲風行地復古改制,認為“秦以前復名蓋寡,遂禁復名”,并直接下詔對單名、復名進行褒貶。然而王莽掌權的時間畢竟短暫,不可能將他的號令統一實施于全國各地;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“二名之禁”,在這15年中,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實行,15年之后,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潰,其禁令不可能會對以后三百年的歷史再發生影響。故,王莽“二名之禁”并非是促使東漢、三國盛行單名的根本原因,而只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
版權聲明: 本文收錄于網絡,如有侵權請E-mail聯系 http://www.hbjnzz.com/ 站長!
標簽: 別號 名字